
河南省上蔡县五龙乡的熊桥村
是人们口中的“艾滋村”
上世纪90年代末
村子里人多地少
难以维持生计
为了供孩子上学
卖血成了村里人补贴家用最快捷的方式
卖一次血能拿到45块钱
在当时的人眼里
这已经是一笔巨款

熊富贵和老伴是熊桥村最早感染艾滋病的村民
疾病几乎拖垮了这个家庭
老两口住在一间破败的砖房里
家里没任何家具和电器
他们只能靠地里的收成勉强维持生计

老人说
他的大儿子和大儿媳也是因为艾滋病去世
说着说着
老人哽咽了
脸上满是绝望

十年时间里
200多人因为感染艾滋病相继死亡
几乎每一家都有艾滋病人
身体健康的人因为惧怕早早离开了村子
剩下的都是老人和病患
整个村子死气沉沉
没有一点生气

熊富贵最小的儿子熊四民
和父母哥哥嫂子一样
也不幸感染上了这个病
儿子因为母婴传播
一出生就成了艾滋病的受害者
孩子走的时候才8岁
全家只有熊四民的大女儿幸免于难

提起十年前那场席卷全村的灾难
熊四民至今仍记忆犹新
十年前
人们对艾滋病并不像现在这么了解
许多村民一听到艾滋这两个字
有直接喝药的
有投井的
也有吓得连夜从村子逃走的

在熊家一家六口都感染艾滋后
熊四民开始借酒消愁
至今
儿子去世 都是笼罩在他心头的阴云
在意志消沉的日子里
他一度想放弃自己的生命

熊四民说
自己曾经有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但他没有抓住
熊四民曾是熊乔村第一批外出打工的青年
他来到北京
在中国人民大学食堂做帮工
熊四民文化程度不高
在人大的这段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原本打算在学校干到转正
但是兜兜转转
他还是回了老家
后来就感染上艾滋
每每说起此事
熊四民脸上只有无奈的苦笑

2004年
当地政府开始对艾滋病患者实行免费抗病毒治疗
绝望中的熊四民夫妇看到一线生机
夫妻俩强打精神
靠养猪维持生计
2010年
熊四民用所有的积蓄翻修了老屋
他希望
如果自己哪天和妻子不在了
女儿一个人也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

为了让女儿考上大学
走出艾滋村
尽管身体经常不适
熊四民依然干着最重的农活
他最大的愿望
就是活着看到女儿走进大学校门

村民张梅英的丈夫熊自成2002年被确诊为艾滋病
2003年
他们的长子熊长永也被查出感染了艾滋
为了让家里唯一的高中生
也就是他们最小的儿子考上大学
熊自成拖着重病的身体外出打工

十年前
熊自成接受节目组采访时
镜头前的他
一直保持着乐观的笑容

但是他内心的担忧
对病痛的恐惧每天都在折磨着他
他怕自己已经没有太多时间
怕自己无法供小儿子考上大学
但他的担心从来不会跟儿子说
这个父亲把所有的苦闷咽进肚子里
病情稍有好转
他就继续下地干活

那时
政府每个月发 给每个艾滋病人100多元的特制票券
票券可以用于看病用药

最艰难的时候
熊自成经常偷偷把票券换成真钱
给在城里读书的小儿子送去

为了父亲的身体
小儿子也有过放弃学业的念头
但他不敢告诉父亲
因为他知道
父亲在用自己的命给他拼一个未来
他不敢让父亲失望

背负着沉甸甸的希望
2004年
小儿子考上了哈尔滨商业大学土木工程专业
成为村里第三个考上大学的学生
接到儿子录取通知书的那天
是他这辈子最开心的一天
他笑得合不拢嘴
脸上是藏不住的骄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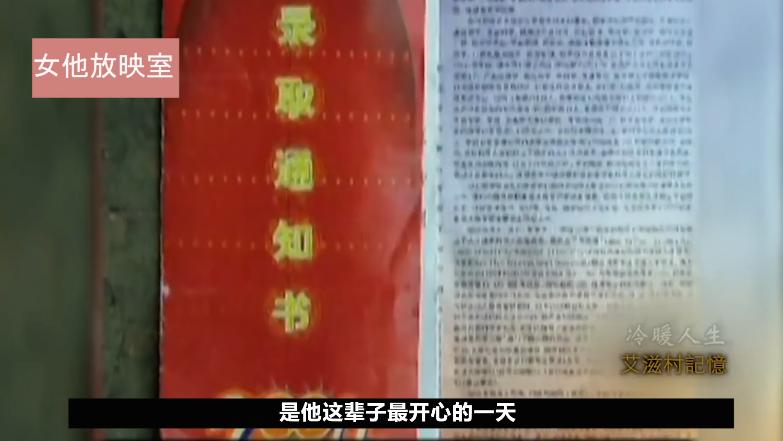
虽然还欠着许多外债
家里的老屋也倒了
一家人只能借住到亲戚家里
上万元的学费对这个家庭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
为了给儿子凑齐上大学的学费
父亲拿着票券和现金
挨家挨户地找人借钱
节目组也为小儿子联系了一些善心人士
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
这个男孩
终于一步步走出了艾滋村

在哈尔滨
儿子收到了来自父亲的一封信
父亲在信里嘱咐到
一定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不要辜负那么多人对你的帮助
没想到 这唯一的一封信
竟成了父子间最后的诀别

2006年7月
熊自成疾病发作 与世长辞
享年57岁
最后的时刻
熊自成像是有千言万语要对儿子诉说
但他已经虚弱地说不出话
如果父亲还有什么遗憾
也许就是没能看到儿子大学毕业
结婚生子吧

当记者离开熊富贵家时
他嘱咐两位老人
好好活着
老人站在屋门口
不停地向远去的记者挥着手
记者不知道
下一次再来熊桥村拜访
是否还能看到这些熟悉的脸庞

村里的路边满是光秃秃的树枝
破旧的房屋
十几年来
熊桥村一直没有变过
还是一样的庭院
一样闲聊的村民
一样靠着墙根晒太阳的老人
只是这里的人们上演着一幕幕悲欢离合

对于艾滋病
了解和预防永远是第一位的
只有正确认识艾滋病
不歧视 不逃避
才能防患于未然
这里是女他放映室
我们下期再见






